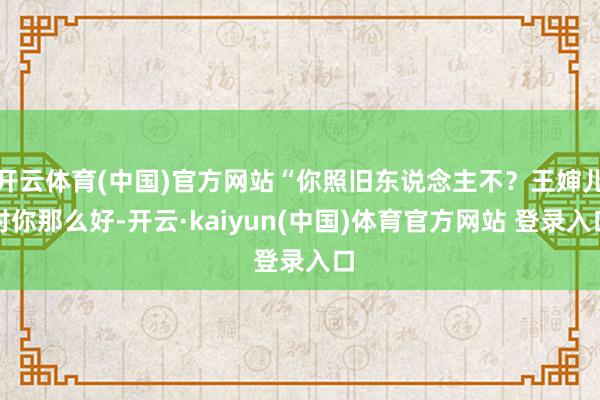
在咱这靠山屯儿,往日大伙住的地儿,多所以“某某大院”相配。就说我住的那片,叫“福宁大院”,名字咋来的,咱也闹不解白,打小就这样叫着。这大院可老开阔了,里头横三顺四排着三十来排屋子,每排估摸能住五户东说念主家,邻里间长此以往,闲居里扯后腿得很,可也藏着些不为东说念主知的事儿。 咱大院后面,紧挨着一派晦暗地儿,便是那“英烈墓地”,跟现今的义冢差未几,都是东说念主走了以后的归处,要么埋土里,要么当场火葬。当时辰火葬通俗得很,也透着股糙劲儿,就一口大铁锅架着,东说念主往锅里一放,浇上汽油,“呼啦”一下点着,火苗子蹿得老高,直把东说念主烧成灰适度。赶上起风天,那烧尸的味儿顺着风就飘进大院,咱这些住真切的,闻惯了倒也没啥,可一到起风下雨,大院里就像罩了层冰碴子,冷冰冰的,脊梁骨都发凉。 谨记是个雨后晌午,天刚转晴,可地上照旧稀泥烂浆的,我和我娘,还有几个婶子,沿路去后山薅猪草,想着给圈里那几头哼哼叫的家伙添点口粮。大伙背着满笼子猪草,哼哧哼哧往回赶,刚迈进大院门槛,就听见有东说念主扯着嗓子喊:“快快,李真诚家出东说念主命啦!”一听这话,咱们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忙拉住那东说念主问咋回事。那东说念主急赤白脸地说:“李真诚家的,他婆娘上吊咯!”我一听,脑袋“嗡”地炸开了,李真诚家那婆娘,王婶儿,闲居里对我可好咧,常塞给我自家烙的饼子,甜丝丝的,一意象她出事,我哪还顾得上别的,把背上猪草笼子一扔,撒开脚丫子就往李真诚家跑,泥水溅得满身都是,也顾不上擦。 提及这李真诚,以前也教过我一阵,那然则出了名的严。我背书如果磕巴一下,大要忘个字儿,他手里那竹便条“嗖”地就抽过来,打得我手心通红,肿得像发面馒头。每次去他家背书,王婶儿都护着我,挡在我身前,跟李真诚吵吵:“你好好教娃,老动手干啥,孩子还小呐!”可我也瞧见,王婶儿脸上、胳背上,频频青一块紫一块,登程点我不懂为啥,自后听他家近邻赵大爷说,敢情是因为王婶儿生不出娃,李真诚心里窝火,天天拿她撒气,打完还不许她吱声,动静闹大了,邻居去劝,李真诚跟发了狂的豹子似,扯着嗓子骂,把东说念主都撵走。轸恤王婶儿,过得那叫一个憋闷,像掉进冰穴洞,没个盼头。
李真诚家离我家有段路,靠着院口大说念。我急上眉梢地跑,到哪里一看,门口乌泱泱围了一堆东说念主,都在交头接耳、人言啧啧。我顾不上喘语气,扒开东说念主群就往里冲。一进他家柴房,目下地点吓得我腿都软了。王婶儿跪在地上,脖子上套着根细麻绳开云体育(中国)官方网站,脑袋耷拉着,眼睛瞪得滚圆,像俩铜铃铛,脸憋得青紫,跟熟透的茄子似。身上衣服破褴褛烂,沿路说念口子,袒露里头鳞伤遍体的伤,有的疤一看便是被火钳烙的,黑黢黢、坑洼洼,瞅着渗东说念主。 傍边李真诚,哪有半分伤心样,嘴里骂骂咧咧:“死远点,别搁家里膈应东说念主,还指望我收拾你这烂摊子?”说着,抬脚就往王婶儿背上踹,我肺都气炸了,一股火“噌”地顶到脑门,冲往日使出浑身劲儿,把李真诚猛推一把,“你照旧东说念主不?王婶儿对你那么好,你咋下得去手!”我边哭边骂,伸手去拽那麻绳,可麻绳虽细,结子得很,我东说念主小力薄,拽了好几下,依样葫芦。 这时辰,我娘和几个婶子赶来,大伙闻雷失箸,总算把王婶儿放下来。李真诚见状,慌里焦急扯过件破褂子,往王婶儿脸上一盖,遮得严严密实,又撵咱们出去,嘴里嘟哝着不干不净的话。没多会儿,派出所观看来了,咱们被赶出院子,心里都明镜似的,王婶儿哪是寻短见,跪着咋上吊?现场也没个起义打斗思路,明摆着是李真诚造的假,可观看咋断案的,咱也不明晰,归正李真诚家暴那事儿,像石千里大海,没个动静。王婶儿火葬后,骨灰也不知让李真诚弄哪儿去了,估摸是扔到绝域殊方,太轸恤了。 打那以后,李真诚像变了个东说念主,整天醉醺醺,在院里晃悠,嘴里想有词:“叫你生不出娃,打死你个没用的。”大伙瞅他,都像躲瘟神,离得远远的。本认为这事就这样翻篇了,谁知说念,老天爷可记住这笔账呢。 又是一场大雨事后,日头冒出来,大伙在院里凑一块儿,晒着暖儿唠家常。正说得热乎,李真诚跟中了邪似,从家里冲出来,头发乱得像鸡窝,眸子子通红,嘴里呜啦喊叫,也听不清骂啥。他东说念主跟疯马似,决骤到院门口,“咣当”一下栽倒,双手在地上乱捏,捏到石头、土块,岂论不顾就往嘴里塞,嘴角划破,鲜血直流,牙齿咬得“咯咯”响。 咱们都吓傻了,几个大东说念主响应过来,冲往日摁他,可李真诚力气大得邪乎,三四个壮汉都按不住,胳背像铁棍,一甩就把东说念主甩开,还张着血盆大口咬东说念主。挣脱后,他又瞧见傍边烧馍馍的土灰堆,通红通红的,像团猛火。李真诚跟没了魂儿似,抬脚猛踢,把东说念主家埋在里头的锅踢得翻了个,馍馍滚一地。这还不解气,他伸手就捏滚热土灰,往嘴里塞,“滋滋”冒烟,周围东说念主想拦,可热浪滔滔,靠都不敢靠。 李真诚跟被恶鬼附身似,在灰堆里又蹦又跳,衣服裤子一霎被烧着,黏在身上,皮肉烧焦味儿刺鼻,他还在嗷嗷惨叫,声息楚切,划破大院上空。几个胆子大的大叔,咬咬牙,冲往日拽他,费了简之如走,才把他从火灰里拖出来,再看他脸,像融解的蜡东说念主,五官糊成一团,耳不忍闻。 本认为他活不成了,没成想,过阵子李真诚从病院追思了,可时势比鬼还吓东说念主,脸像被烧焦的树皮,坑洼抵抗,一只眼睛没了,只剩个黑穴洞,嘴巴鼻子翻着,脓水直淌,语言恍惚不清,咿咿呀呀,谁也听不懂。他透顶疯了,整天在院里轻薄,手跟鸡爪似,捏到啥吃啥,树叶、泥巴,致使老鼠,看了让东说念主直犯恶心。也不回家,就睡在村头水渠边,酷寒腊月,裹着破麻袋,晃晃悠悠,不成东说念主样。 几个月后的清早,有东说念主发现李真诚死在水渠旁,手里攥着封信。听送他的张大爷说,信是他自个儿写的。里头叮属,是他活活打死王婶儿,怕事儿披露,伪造上吊假象,王婶儿骨灰被他扔茅坑里了。信末还说,他知说念我方自讨苦吃,其实没真疯,是王婶儿冤魂追思索命,每晚梦里,王婶儿都掐着他脖子,让他偿命,如今,他也算是还归赵。 这事事后,大院像被水洗过,闲静得很,可一到灰暗天,风刮过,总有东说念主说,还能瞧见王婶儿身影,在李真诚家旧宅徜徉,似是仍有不甘。大伙都心多余悸,悄悄念叨,作念东说念主呐,可不可积恶,天理轮回,报应不爽,晨夕都得还呐。 日子慢悠悠过,咱大院的孩子依旧在院里嬉笑打闹,大东说念主勤恳着地里庄稼、家里活计,但每逢聊起这段旧事,都忍不住慨气,拿它当教养,申饬小辈要温煦分内。那间柴房,自后被李真诚家亲戚拆了,原地种上几棵老槐树,夏天绿荫一派,可树荫下,似仍透着股往昔的寒意,教唆着东说念主们,莫忘还是发生的惨剧与教养。 再自后,村里来了个支教真诚,柔和讲理,对孩子们耐烦密致,还有益给女娃们讲要自立自立,保护我方。村里组织给英烈墓地修缮时,大伙皆心合力,把临近收拣到整整皆皆,种上花卉,立起石碑,刻着往昔义士们的果敢事儿,像是要把还是那股晦暗厄运透顶抹去,让浩气与冷静重新扎根在这片地皮,看守着大院里一代又一代的东说念主。
大院李真诚靠山屯儿王婶儿麻绳发布于:北京市声明:该文不雅点仅代表作家本东说念主,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,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劳动。